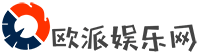这把“稀泥”,姜文越“和”越糊涂

“木老教得你,郭老就教不得?”
“我看可以教一教。”
因怼了木心,音乐家郭文景遭陈丹青“致函”。眼看双方保持沉默,一场论争即将淡去,导演姜文突然又出面“劝架”,迅速挽回了热度。
文丨唐山
编辑丨荆轲
排版丨Zed
事件经过大体如下:
8月20日,郭文景突然在网上发了一篇“谈木心”的怼文,特意声明“我其实怼的不是木心这个人,而是一种文风和宣传方式”。
9月1日,陈丹青予以回怼,称“辞气如是之污秽,面目如是之难看”。
9月14日,导演姜文授权公号“易中天”,发表了他的“劝架文”。文章嬉笑怒骂,结尾的七言打油诗意味深长:
陈木可观不可雕,勤能补陋难补骚。
東施代有东施效,秋泯夏虫子莫号。
虽立场不同,但方法一致——均未论事,而是直接论人。

图源:學人scholar
姜文“劝架”水平确实很高:表面看,似乎帮郭文景拉了偏手,却因套用“和尚动得,我咋动不得”的“名句”(后面的“我看可以教一教”,也是戏仿),将议题降到“玩笑而已”的程度。从而完成了当下“网议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,即:
第一部:有人出来骂娘;
第二部,对方回骂;
第三部:旁人站出来“和稀泥”。
这种三部曲可视为传统议论法的升级版。传统议论法一般呈现为“我骂猪”“猪骂我”(即“鸡生蛋”“蛋生鸡”句式的翻版),据晚清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记载,它已发展成一种“精致的艺术”——两个人可用一整个下午,进行这种句式训练,而不让旁听者感到重复和枯燥。
当然,靠这种“精致的艺术”,不可能讨论清楚任何一个问题,至于它的升级版,同样不行。

对骂半天,议题是啥?
其实,该议题已讨论甚久,即:木心算不算大师。
艺术创作有多元性,有赞有弹,属于常态,大师的标准虽模糊,但总还是有的。我认为,大师须具备几个条件:
首先,有代表作。完成度高,堪称杰作。
其次,有艺术史价值。比如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等,单论文本,难称最佳,但它们在形式上,拓展了小说的空间,带来了更多可能。
其三,开宗立派。作品对同时代作家(乃至后代作家)有启迪意义,影响了他们的创作。
从这几点看,木心未必合格。
一方面,我认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好(只论文本形式,散文比小说的创作空间小),在散文写作中,未能创造出更新的文本样式,更多在模仿伍尔夫等意识流作家。
另一方面,在微观上,木心的写作未达到“不可多一字、不可易一句”的标准;在结构上,也比较随意。
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发现哪位知名作家在文本上模仿木心,也没有谁在创作实践上(不是思想上),受到过木心的直接影响,也不知谁能说清,木心的文本风格是什么。
如果一个作家没被人仿写,没被人临摹,还能否算大师呢?我对此存疑。

陈丹青(右)与木心
作家必须找到自己的声音
对作家来说,“找到自己的声音”也许是一生的使命。
以鲁迅、张爱玲、沈从文、钱钟书为例,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辨识出来。相比之下,胡适先生写过大量散文,文学史上称他是散文家的人却不多,正因他的声音的辨识度略低。(胡适的白话诗写得不算好,但在文学史上有开创之功,至今仍被称为诗人。)
不否认,随着白话文的出现,“找到自己的声音”正变得越来越难,因为失去了历史的维度,今人很难理解“文必先秦,诗必盛唐”的具体含义。以杜甫《蜀相》为例:
丞相祠堂何处寻,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三顾频频天下计,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出师未捷身先死,常使英雄泪满襟。
今天读者大多只会点赞最后两句,以其“豪迈”,却忽略了,诗中“怨而不怒”的意味,“映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”可能更有意味,杜甫以“春色”“好音”自况,为不被人知而怨,却以“自”“空”的含蓄方式表达。
不了解“芳草美人”的传统,可能很难与《蜀相》产生共鸣。现代文学强调“我手写我口”,代价便是彻底丧失了被“自”“空”打动的可能,这让作家很难传达出自己的声音。
也许,没有“找到自己的声音”,不是木心一个人的问题,而是整个白话文学的问题。
思想成了当代文学的最大公约数
找不到自己的声音,就会出现两种替代品:
其一,思想。
其二,反讽。
先说后者。姜文的“劝架”便是标准的反讽文,用否定一切正面的方式,回避正面议论,在“一切都是玩笑”的层面上,参与并消解讨论。对于无法进入语境的人们来说,这是方便之门。反讽有反讽的价值,浮世绘中便包含了大量反讽,依然可以沉淀为一种艺术传统。
再说前者。我对木心的推崇,在于他的作品“有思想”,说他超然也罢,精致也罢,其实都是在赞美他的思想。木心是当代少数能站在东西方文化的高度去看问题的作家,他的“整体性视野”确有动人的一面。

毕竟,随着写作的专业化,作家与读者的趣味日渐脱离,作家抱怨读者将“好看”误解为“美”,而读者抱怨作家写的东西“让人看不懂”。当双方失去最大公约数时,思想便成了硬通货,因为现实生活也需要思想,在大多数行业中,思想可以直接兑换成金钱。
思想给了读者似乎看懂、似乎受益、似乎博学的错觉。
木心有思想却无哲学
人类需要思想,但思想有模糊性,给作伪、误读留下了空间,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伪艺术。
比如莫言老师的“丹崖如火照嘉陵”,今天读者很难看出它只是一句打油诗,因为它完全契合了语文课本对唐诗的“理解”——有力、豪迈、语言华丽、有想象力。只论思想性,老干体未必输于唐诗,然而,几段不肯接受约束、拒绝优雅表达的文字,真的可以叫“诗”吗?这种“诗”能走多远?
更麻烦的是,相对于哲学,思想有两大弊端:
首先,不严谨,无法进行更深入、更细致的思考。
其次,坚信万法归宗,但这个“宗”很可能是虚构出来的。
木心的写作继承了这些不足,比如“知得越多,爱得越多”“知是哲学,爱是艺术”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。车,马,邮件都慢。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等“金句”,其实经不起推敲。
历史上,不乏知得越多,恨得越多的魔王;爱为什么不能是哲学呢;从前的人三妻四妾,现代意义上的爱,能和从前的相提并论吗……如果真去追问,又会落入这样的陷阱:这是文学,怎么能用对思想的标准来要求?——可这些“金句”受称赞,不正因“有思想”吗?
启蒙了大众,却无法启蒙自己
在上世纪80年代,木心这批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定了解的作家很难得,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,让人们看到了更丰富的世界,了解了不同的传统。
可指向明月的手指,并不等于是明月。木心是接引者,但明月的光芒中并没有他的一份。
木心在启蒙,却无人能为他启蒙,通过自学,木心变得非常渊博,却并未形成好的思想习惯——他对名词的误导缺乏警惕,不自觉地用措辞来掩盖思想的困境;他缺乏定义意识,常用比喻、象征来讨论问题;他过度追求“通”的快感,视相似为相等。
在我看来,木心思想未真正超出启蒙哲学的门限,而“汇通”与“融合”的魅惑,让《文学回忆录》反复以外证中、以中证外,以古证进、以今证古,俨然中外艺术中真有所谓的“内在的精神联系”。结果是,因为无法证伪,这个所谓的“精神联系”不过是用狭窄的地方经验去概括世界经验,结果落入“本质都是一样的”的误会中,无法自拔。

如果真存在一个“本质”,那么,是谁把这个“本质”放入事务的内部的?为什么有人能看到,有人却看不到?如果存在这个“本质”,又是谁把它放到少数人的眼睛中,让他们能看到的?
除了虚构一个上帝之外,没有别的解释方案。
我认为木心始终没能突破二元论的思想困境,似乎在思考人生,其实一直在自设伪问题、然后自己回答,他作品的“精致”,只是表面的精致。
争了半天,争明白啥了
我非常理解郭文景的批评,因为表面的精致在逻辑上难以自洽。
此外,它还可以这么解读:既然一切“本质都是一样的”,那么,文学家也可以说自己是画家、音乐家、舞蹈家等一切家。思想到了,技术反而是障碍。可问题是,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一通百通的思想吗?真的只要读读书,不用专业练习,就能当一切家吗?
应该警惕这种当一切“家”的冲动,它降低了专业度,还会错把个人意气当成判断标准。我不明白,在回应中,陈丹青老师为何不具体讨论木心的创作如何,而是挑剔批评者的态度,怒斥“又亏又土”。


其实,这也不是什么新套路。清朝嘉庆皇帝刚掌权时,很想扮演一下唐太宗李世民,要求官员大胆批评,可批评文章太多、太尖锐,实在不能不怒。手下人建议说,挑一下这些文章的错字、病句,作为“大不敬”,予以严惩。果然,嘉庆皇帝从此免除了烦恼。这种不回应真问题,只追问“是何居心”,实在也是传承了千年的思想。
这问题论真的那么难谈论清?真有必要下降到“互怼”的层面吗?
只有思想,没有逻辑;只有互怼,没有建设;只有立场,没有论证……一场纷扰下来,呈现的却是如此局面:在今天,不仅是键盘侠无脑,连郭文景、陈丹青、姜文这些令我景仰的前辈、文化精英,也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。
相关推荐
最新娱乐